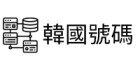我不利(Michel Maffesoli)精彩的《部落时代》(1996),尤其是他通过将新兴的参与形式解读为他所谓的“新部落”,对“日常政治”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化。“新部落”或“后部落政治”的部落隐喻与吉兰(Gillan)的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而马菲索利对政治权力形式(他称之为“权力” 或“内在”权力)和政治合法性(他称之为“地下中心性”或“自下而上”的合法性)的关注,为解读“另类”和“主流”参与形式提供了一种新颖且富有创新性的方式。然而,个人主义的阴影再次出现在吉兰的反思中:
但在主流政治渠道之外,那些自学成才的激进主义者早已意识到,“年轻人和穷人”并非一个同质 Viber 手机数据 群体,即便他们同样面临着不稳定的客观条件。或许他们也意识到,即使存在一个有效的不稳定群体政党,其对年轻人和穷人有吸引力的单一维度,也正是其在一系列其他政策领域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这引出了吉兰对互联网的关注
,他认为互联网并非克服个人主义或基于议题的政治,而是拥抱它们,并将它们所鼓励的商议转化为服务于(本质上是集体的)政体的方式。他当然正确地指出,在《捍卫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我确实以极具争议性的力量驳斥了“数字民主”。尽管我强烈 信息图设计是一个瓶颈 反对“回音室”和“网络公民”,但吉兰借鉴了杰弗里·朱里斯和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的理论,对互联网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释,揭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纽带。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线运动“开始重新构想不同的生活方式,重新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并重新定义如何使民主发挥作用”。本质上,吉兰认为批判性社会运动正在打造新的在线群众动员形式,并有能力改变民主政治。
那么,接下来的讨论会如何发展呢?我该如何回应我之前学生那篇精彩的文章?两者的重合点和争议点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
简而言之,我认为我和凯文
·吉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和规范鸿沟,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新加坡电话列表 之间似乎已经出现的隔阂。我很乐意尝试通过进一步的对话,甚至可能的合作,来弥合或弥合这一鸿沟,但他反思的字里行间,潜藏着某种“悲观主义政治”的意味。我对这个话题的思考尚处于萌芽阶段,但似乎主要围绕着个性、节奏和人的主题。吉兰的分析似乎认为,无论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如何,它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我的感觉是,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集体意识,一种对直系亲属之外的社会纽带的自然渴望,以及一种跨越社会阶层、国家和宗教的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吉兰对那些“激进自学成才者”的评论,突显了其主张中不可避免的分裂性,这些人认为年轻人和穷人绝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共同的客观条件——缺乏永久性就业、低工资、不断接受再培训、频繁搬迁等等——或许可以构成一个新政党——“不稳定党”——的基础。但不知何故,“使其吸引年轻人和穷人的单一维度”也成为使其“在一系列其他政策领域存在问题”的特征。但这是为什么呢?吉兰为个体化、基于议题的活动家辩护,理由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考虑到关注点与一系列更广泛议题的重叠,那么,为什么不稳定党不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类似的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