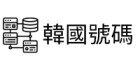我并没有在大英图书馆进行公开演讲,我只是发起了一场对话。
因此,当我以前的学生凯文·吉兰博上发表了这场对话的最新一期时,我感到欣喜和满足。现在,有些学者可能会对一位以前的学生试图在如此开放和易于理解的领域挑战他的前教授的想法嗤之以鼻,但我要说“干得好,这家伙!”凯文总是有点儿活跃,但他试图颠覆我的论点和想法,从经验和规范的角度深入我的逻辑核心,读起来真的是一种享受。
让我欣慰的是,吉兰的方法并不关心如何磨刀霍霍来攻击我的论点,而是关心如何通过引入批判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见解来强化我的论点。
从吉兰的角度来看,我提出的
民主问题”问题在于我的分析视角过于狭隘。我公开谴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民主或政治想象力的丧失……我们重新构想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我们与周围人重新建立联系的能力;我们重新将挑战解读为机遇的能力,或者我们重新定义如何理解和使民主发挥作用的能力”[原文斜体],但 WhatsApp 号码数据对吉兰来说,这种论点反映出我未能超越标准框架。“政治想象力已经在主流之外得到运用,”他辩称,“在另类全球化和社会论坛运动的发展中,以及最近在西班牙的愤怒运动以及欧美各地公共广场的占领者中。”
基于这一基本论点,吉兰继续强调三个问题——代表性、制度变革和互联网——这些问题为我在最初的演讲、播客、文章、T 恤等中发现的问题增添了额外的色彩和质感。
诚然,我最初的演讲中几乎没有提及“代表制”的概念,但正如吉兰所说,“它正出现在那些将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作为其行动主义一部分的人的视野中”。然而,这里值得关注的反思并非仅仅关注“代表制”的概念本身,而是将其与我最初对市场驱动的个体化及其对集体社会价值观的腐蚀性影响的批判联系起来。然而,吉兰揭示了一个类似的悖论,即许多当代批判性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在于无政府主义,尽管对许多抗议者来说,这或许并非一个相关的依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符合他们对个人作为权利主权拥有者所持有的深切尊重。这一论点与威廉·盖尔德纳 (William Gairdner) 在《民主的麻烦》 (2001) 中的观点相呼应,但如果无政府主义所激发的价值观和实践确实“在当今大多数批判性社会运动中超越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影响力”,那么《代表制的麻烦》对吉兰来说则认为,主流之外的“新”政治很大一部分都渗透着其自身的个人主义形式,这与民主集体行动的逻辑相悖。
制度变迁的问题同样棘手正如吉
兰所描绘的,一个日益错综复杂的制度架构,职能和职责分散在多个治理层 新加坡电话列表 级和多种类型的组织中。不可否认,这片土地的地形错综复杂。在《无序行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我试图绘制这片土地的地图,但其结构如此模糊不清且流动性强,以至于我所能绘制的仅仅是一幅粗略的地形图。鉴于此,公众从主流政治和政党转向某种基于问题的行动主义,可以被视为完全合理的。如果说存在问题,那么在吉兰的分析中,问题不在于公众,而在于代议制民主的主导制度结构未能跟上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步伐。 “因此,代议制民主的主导制度结构,即地理代表制和政治部落代表制的混合体,本质上对士在曼彻斯特 液态现代社会 令人难忘 的居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对许多人来说,需要的不是教育(我对民主弊病的主要处方),而是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