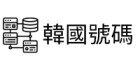布兰肯纳格尔教授的第一个批评无异于自相矛盾。 他认为,俄罗斯宪法“绝不是一元论地服从于”国际法。(第961页)他表示,宪法第15条(我在文章中引用该条作为“俄罗斯1993年宪法否定了苏联对国际法的二元论方法”(第935页)的证据)“并不像卡恩所声称的那样,意味着俄罗斯对国内法和国际法持有一元论的理解”(第962页)。我因忽视第17条和第79条而受到批评,而布兰肯纳格尔教授似乎认为这两条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一元论与二元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引用自己喜欢的学者和实践。但 我的文章绝对不打算解决这个问题。布兰肯纳格尔教授强调二元论国家需要依法批准条约。但无人质疑《欧洲公约》已根据俄罗斯法律获得批准。同样毫无争议的是,俄罗斯自愿且未作任何保留或减损地接受了欧洲人权法院(根据《公约》第32条)对“涉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解释和适用的一切事项”的管辖权,无论是在国家间案件中还是在个人申请中。
那么为何俄罗斯会延续苏联时期对
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呢?这或许会引出一些有趣的反事实,探讨俄罗斯如今是否会批准《欧洲人权公约》。但这并不是我所写的文章;这样的讨论引发的政策问题多于法律问题。(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与伊琳娜·布西吉娜教授合著的一篇新文章,可在此处查阅。)毋庸置疑,俄罗斯在二十多年前批准这些国际法律义务时,就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而如今,在试图摆脱其影响之际,它显然正在重新评估这些代价。
布兰肯纳格尔教授抱怨“西方”虚伪地对俄罗斯实行“双重标准”(第965页,注17)。但这又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借口。事实上,布兰肯纳格尔教授似乎相当宽容地提出了在俄罗斯问题上应给予特殊考虑的问题:“如果大多数 欧洲数据 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都得到执行,那么默许某些裁决不予执行或许是合理的?”(第968页)。这个问题应该由政客和外交官来回答,而不是由律师或其客户——俄罗斯侵犯人权的不幸受害者——来回答。
俄罗斯历史课
布兰肯纳格尔教授热衷于指出俄罗斯过去遵守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历史。尽管他称我为“俄罗斯批评者”(第 967 页),但我衷心同意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带来了很多好处。那些熟悉我的学术的人会记得我曾写过这些对俄罗斯法律改革的有益影响(例如 这里、这里和这里)。但我还认为,就对斯特拉斯堡的机构和程序整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言,这并非没有代价的过程。例如,俄罗斯不仅是旨在减少主要由俄罗斯造成的积压请愿书的第 14 号议定书程序改革的催化剂之一,也是这一变化以如此令人沮丧的缓慢方式生效的原因,导致第 14 号议定书之二不得不通过,而俄罗斯实际上却阻碍了改革进程。
因此,布兰肯纳格尔教授的“简史”并非不受欢迎,但并非特别必要,也并非完整。布兰肯纳格尔教授构建(然后又推翻)了一个稻草人模型,把我描述成“又一个不太令人信服的声音”,在一片不公正的批评声中,“俄罗斯再次 司的成本由固定部分和 扮演恶棍,西方再次因其拒绝‘遵守规则’——用俄罗斯人的话说,是西方规则——而感到震惊。”(第961页)在布 韓國號碼 兰肯纳格尔教授的回复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克里米亚被吞并或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其他地区军事行动的字眼——显然这些都与他的历史无关。这些针对欧洲委员会其他成员国的暴是围绕俄罗斯宪法 力袭击是对俄罗斯条约义务(更不用说强制法)的令人震惊的违反,而非不公正地强加未经寻求的规范。